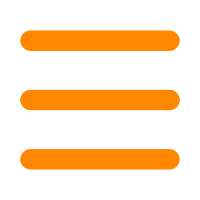一
依据一般时尚的见解,传统的中国社会,从政治学的方面看,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从社会学的方面看,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而无论“人治”还是“礼治”,在今天都不具备超越年代的意义,由于归根到底,它们只不过另一种社会、另一个年代的范畴。在讲求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现代社会里面,这类范畴既不具备正当性,也没办法成为一种积极的精神资源。对繁复的社会事实进行分类和概括,这是大家认识和知道社会的一种基本方法;而且,把传统的中国社会概念为所谓“人治”的社会或者“礼治”的社会,恐怕也不可以说是错误。不过,大家在如此做的时候确实面临着某种危险,那就是把对象简单化和将定义绝对化。事实上,作为一种平时话语实践,“礼治”与“法治”如此一对定义的运用,已经具备某种绝对的意味,这一点不只表目前大家对如此两种社会和秩序所作的截然划分上,也表目前他们对这种区别后面的支持性理论的不自觉上面。为了揭示这种情况,我将从剖析一个社会学家所建构的颇具影响的社会模式入手,通过将有关定义语境化和相对化的方法,达到对这类定义与定义后面的理论的深思,重新把握被遮蔽的社会现实。
二
本文所要讨论的“礼治秩序”的定义源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注: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一书中,费氏试图从中国当地社会里面提炼出一些定义,并用它们来勾画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这类定义包含“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等等。在费氏看来,中国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或者,用社会学家的话说,是所谓“礼俗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面,大家安土重迁,其生活富于地方性。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大家彼此熟知,因此,这又是一个“没陌生人的社会”。(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页。)
在如此一个社会里,“规矩不是法律,而是‘习’出来的礼俗”,(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页。)换言之,乡村社会秩序的保持,在很多方面与现代社会秩序的保持是不一样的。正是着眼于这一点,费氏不以“人”、“法”二字区别“人治”与“法治”,而把它们的分别确定在保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上面。从这里,便产生了“礼治秩序”的说法。
依据费氏的概念,“礼是社会公认适合的行为规范”。(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0页。)不过,仅就好为规范这一点来讲,礼与法律无异。二者的不同在于,法律要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礼却无需有形的权力机构来保持。“保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0页。)通过教和学而代代相传。在缺少变动、代代如是的乡土社会,过去的经验常常可以用来作现下生活的指南,大家因此对传统抱有敬畏之感。作为所谓“合式的路子”的礼,即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3页。)而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5页。)如此的秩序自然要强调塑身,倡导克己,和重视教化。有了纠纷,要用调解的方法来解决,打官司是可耻事情,由于那表明教化不到。
“乡土社会”所描述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情态,“礼治秩序”所代表的则是一种秩序种类,二者之间具备紧密的内在关联。用费氏我们的话说,“礼治的可能需要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对生活问题为首要条件,乡土社会满足了这首要条件,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保持。”(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3页。)相反,在一个变迁的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没办法保证,只有大伙在规定的方法下合作,才可能成功地应对一同问题,如此便产生了对法律和法治的需要。换句话说,“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一样的社会情态中。”(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3页。)礼治社会是乡土社会的特点,法治则合适于变迁非常快的社会和年代。社会情态改变了,秩序种类也势必要发生变化。
费氏在他的书里面并没正面地和系统地论述法的理念,但他的“礼治秩序”定义却是在一个与之正相对应的定义即“法治”的对照下拓展的。事实上,无论“乡土社会”还是“礼治秩序”,都只有在一个历史的和比较性的框架里才是有意味的和可以理解的,而大家也确实可以从费氏的比较性论述当中理出一个“礼治”和“法治”的对比式来:在“礼治秩序”这一面,维系社会秩序的规范是礼,保持礼的力量则是传统和习惯;礼对于人的约束是内在的,即人通过教化而主动地服膺于礼;这种秩序重视塑身和克己,依赖调解来解决纠纷;打官司被视为丑事,讼师更为众人所不齿;与这种秩序合适合的是一个缺少变化的社会,或者,用愈加确定的说法,一个前现代的社会或传统社会。而在“法治”这一面,基本的规范是法律;法律靠了国家力量来推行,从外部对人加以约束;法律着眼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因此鼓励大家倡导各自的权利,亦不以涉讼为耻,相反,专门的法律家如律师在这种社会中占有要紧地方;自然,与法治合适合的社会是一个变迁非常快的社会,即大家所谓现代社会。假如把上面的对比式再加以简化,大家可以看到如此一组正相对应的定义:礼治/法治,礼俗/法律,习惯、传统/国家权力,内在/外在,强调克己/倡导权利,调解和教化/诉讼和审判,讼师/律师,相对不变/变动非常快,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等等。
对乡土社会的刻画和对礼治(秩序)与法治的区别,自然能够帮助大家认识和知道中国的社会现实,但这未必是作者唯一的和最后的目的。在费氏考虑和写作这本小书的时候,中国社会正处于变化和动荡的转型时期。
就其讨论的主题来讲,一个引人注意同时也是让人感到困窘的问题是,现代的司法规范已经引进并且推行下乡,乡土社会中人的组织、行为和观念却没发生相应的变化,结果是“现行的司法规范在乡间发生了非常特殊的不良反应,它破坏了原有些礼治秩序,但并不可以有效的打造起法治秩序。……结果法治秩序有哪些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8-59页。)要解决如此的问题,依据费氏的怎么看,除去把现代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以外,还应当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有一番改革。由于,归根到底,只有破坏了原有些乡土社会的传统,才可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8页。)
费氏的问题意识非常了解。因为中国社会所历程的转变,礼治秩序已经失去了它的历史正当性,而且事实上,它也正在为法治秩序所取代。因此,问题只是,怎么样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完成这一社会转变,同时尽可能防止社会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害。应该说,费氏当日对中国社会所作的察看是敏锐的,而他对于中国社会进步所抱持的这种怎么看,即便在今天仍然是颇具代表性的。(注:费氏的这本小书自80年代以来一直获得重印,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不过,在这本小书问世将近半个世纪之后,面对新的社会理论与实践,大家好像有责任也有理由重新考虑这一问题。
三
大家的反省可以从办法论开始。
费氏对于他所谓“乡土社会”的描述一方面打造在社区察看的基础上面,其次也遭到他对于中国社会一般知道的支持。不过,正如他一个人在《乡土中国》的“重刊序言”中所说,这本小册子与他以前所写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如《江村经济》等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定义”。
这类定义可以帮助大家一般地知道“中国基层传统社会”,知道它的特质和结构,它的支配着社会生活每个方面的“特具的体系。”换言之,“乡土社会”也好,“礼治社会”也好,这类定义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都具备远为广泛的适用性。问题是,费氏对于中国的直接察看和考虑毕竟是被限制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而这一特定时空又恰好处于中国社会面临现代性挑战的转变过程之中,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传统社会”,于是,费氏对“中国基层传统社会”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真实靠谱,又在多大程度上由于其特定时空内的特殊经验而遭到扭曲,就成了一个问题。(注:譬如,40年代中国的农村社会已经深受现代化进程影响,新试的37法规范也已经推行下乡,这意味着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改变不可以不影响到乡社会生活,影响到乡民针对“法律”的怎么看、态度和行为。)
指出上面这一点并非要不承认传统的连续性,而是想强调,即便是具备连续性的传统也常常在变化之中。历程了近代革命的中国社会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社会固不待言,就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面,秦汉与唐宋、唐宋与明清,其社会形态也都各不相同。事实上,费氏所刻画的“乡土中国”更接近于明清社会。这也非常自然,由于正是明清社会,直接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也是由于这个原故,对明清社会的认知,不只能够帮助大家重新反省费氏建构的所谓“乡土中国”的社会模式,而且对大家认识近期10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大有裨益。
费氏笔下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有两个特征,第一是它比较地缺少变化,所谓“乡土特点”使得整个社会趋于静止;第二是只见“社会”不见“国家”,与相应地,只有“礼俗”没“法律”。这种社会与大家目前所知道的明清年代的社会并不相同。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伴随人口规模的飞速扩大,中国社会的产品经济和货币经济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土地买卖和土地的流转极为频繁,这使得整个社会内部充满动荡与不安。这样的情况表目前法律上面,便是诉讼频仍和地方行政的不堪重负。譬如据一位日本学者的守旧估算。乾隆年间,普通州县一年可能收到15000到20000份状词;在一个有大约23000户人家的州县,每年作为新的原告或被告参与诉讼的千人以上。(注:参见夫马进:《明清年代的讼师与诉讼规范》,范愉译,载《明清年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当然,这种估算即使属实,也并不意味着清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无别,或者,清代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入法治年代。大家可以确定的只不过,明清社会并不缺少变化,当时的基层社会更不是不见“国家”,在那里,社会秩序单靠传统、习惯和礼俗尚不足以维系。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除去上面提到的一般缘由,诉讼频仍的现象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这类诉讼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与,对于体现于诉讼中的社会需要,国家的司法规范是不是可以予以满足?要全方位回答这类问题,显然将大大超出本文的主题和篇幅,因此,下面仅就本文关心的问题,依据已有研究作一个简单的叙述。
清代的诉讼,就其数目而言,多半与所谓“户婚田土钱债”有关。当时,这些事务被国家视为“民间细故”,并将处断的权限委之于州县官吏。然而,对普通民众而言,生活日用无非就是户婚田土钱债一类事情,遇有纠纷,若不可以准时解决,其平时生活势必深受影响。特别是田地房宅一类纠葛,关涉人民生计,故总是拼死相争。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这种利益纷争并不以“权利倡导”的方法表现出来,同样,无论民间的调解还是官府的听讼,也都不是以界定“权利”为目的展开的。譬如诉讼,当事人并非依法倡导其权利,而是以“喊冤”方法求“青天大老爷”为自己“做主”。为此,无论告、诉,状词总要列举他们“恶行”如无理、霸道、欺压、殴打情事,且多夸张其词,期冀引起官府的注意与同情。官府这一面,则以更高道德权威的身份,站在“公”的立场上,在全方位考察和考虑了各种具体原因的基础上,作出不偏不倚、合情适当的判断。(注:参见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年代的讼师与诉讼规范》,范愉译,载《明清年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所谓不偏不倚,就是取中,不偏私;所谓合情合理,即是考虑周全,既遵守当然之理(如“欠债还钱”),又照顾自然之情(如“事出无奈”之类)。(注:参见滋贺秀3、《清代诉讼规范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范愉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年代的讼师与诉讼规范》,范愉译,载《明清年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关于这一问题更普通的考察,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第284-30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因此,在“在理”者未必能获全胜,“无理”者也未必全败。自恃理直而不依不饶的态度和做法本身就会被看成是不近情理而遭受非议。(注:参见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年代的讼师与诉讼规范》,范愉译,载《明清年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
与上述情形相应,民间也并没有与事实上的领有关系相离别的抽象权利与保护这种权利的“所有权规范”。譬如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土地方面,“所有些对象与其说是‘物’,不如说是一种‘经营权’,……土地所有权本身并没成为一种国家的规范。由于所有者的地位并不由国家在他相对于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地方与用途这一规范层次上进行设定和承认,而只不过体目前所有者以前一管业者手里获得的、眼下正在从事或出售负有税粮义务的经营收益与周围大家对这种状况的一般知道和尊重”。(注:参见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年代的讼师与诉讼规范》,范愉译,载《明清年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换句话说,大家今天所谓的“土地所有权”,当时只不过一种打造在某种“来历”的基础之上并且获得一般社会承认的相对稳定的状况,一种介乎权利与事实之间的状况。从规范秩序的角度看,这种状况的稳定性与地方性惯例或大家所谓习惯有关,但即便是习惯法,正如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所表明的那样,也不可以够提供一套脱离开事实的抽象规范。(注:在习惯法那里,规范与事实不可以够明确区域分开来。参见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第43-44页,吴玉章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哈特:《法律的定义》,第92-95页,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其结果,在明清年代,随着着人口的巨大重压,与人口与资源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民间围绕着每个不一样的“生业”而展开的斗争,就呈现出一种你挤过来、我推过去的暗暗较劲状况。(注:在习惯法那里,规范与事实不可以够明确区域分开来。参见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第43-44页,吴玉章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哈特:《法律的定义》,第92-95页,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了解了这一点,大家就不难知道,为何当时的民间纠纷常常拌以各式各样的强力行为,从“图赖”式的“胡搅蛮缠”一直到关涉人命的“争殴”。(注:滋贺秀三过去注意到这种现象,详见其所著《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技巧——以淡新档案为史料》,姚荣涛译,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刘俊文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又,清代刑科题本中“土地债务”类涉及的都是这种情形。详见《清代地租剥削形态》及《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两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目前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
明清年代民间的“户婚田土钱债”纠纷之所以多,除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变化有关以外,也与财产规范和法律规范有关,与大家看待和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关。既然民间各种“生业”只不过一种介乎权利与事实之间的相对安定状况,而不曾在规范上被明确地加以界定,纷争与诉讼便会源源不断。又由于官府的审判事实上与民间调解一样,旨在恢复和谐、解决纷争,并不以界定和保护权利为目的,上述情形便只能进一步加深,以至虽然社会中存在无讼的理想和息讼的努力,虽然诉讼成本极为高昂,纠纷和诉讼仍然有增无已。其实,诉讼成本高昂这一现象本身也能说明问题。说到底,当时的司法规范并非为保护个人权利而设计,假如要在情节琐细且数目海量的民间词讼里面将权利一一界定了解,则将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可以负担。
因此,地方官便不能不倚重民间调解机制,并且把听讼变成教化,将技术问题转变为道德问题。(注:这一点早经黄仁宇先生指出,详见《万历十五年》,第145-1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关于中国古时候法律的道德与问题,参见梁治平注参见滋贺秀3、《清代诉讼规范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范愉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年代的讼师与诉讼规范》,范愉译,载《明清年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关于这一问题更普通的考察,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第284-30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引书第9、10、11诸章。)不过,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那样,如此做的结果并不可以阻止潮水般的诉讼。为了应对冗杂的衙门事务,地方官不能不依靠幕友、书吏和差役。(注:关于清代幕友、书吏和差役的状况,参阅郑秦《清代司法审判规范研究》,第105-14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第631-66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后者数目可观,但却在国家编制以外,他们中间多数人的生活和办公成本由当事人身上索取,由这里,便产生了种种所谓衙门“陋规”。它们令诉讼成为一种灾难,但仍不足以根绝诉讼。
明清社会内部蕴函了很多危机,诉讼频仍与地方行政的困顿便是这类危机的表征之一。
四
清明年代的人比较容易把诉讼频仍的现象归因于民间的“健讼”风习或者讼师的活动,但对于一个生活在20世纪的察看者来讲,这种怎么看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在大家看来,不但诉讼的当事人,而且就是那些从诉讼中渔利的讼师,其行为也未尝不具备某种合理性。事实上,并非“健讼”之风和讼师的存在使得诉讼有增无减,恰恰相反,正是诉讼的必要性促进民众选择诉讼,(注:大体说来,发生纠纷时诉诸民间权威还是官府,这一点取决于当事人对其具体景况的权衡。参见岸本美绪:《清初上海的审判与调解——以(历年记)为例》,载《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台北,1992年版。)并使得讼师可以存在。(注:参见夫马进:《明清年代的讼师与诉讼规范》,范愉译,载《明清年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问题是,诉讼中所体现的社会需要并没获得规范性的解决,结果在一方面,旧的诉由一提再提,新的诉由纷至沓来;其次,海量的诉讼在对地方衙门形成巨大重压的同时,也对当时的司法规范构成挑战。今天看来,这个挑战没办法在传统的规范框架内予以解决,由于它包括了现代性的需要在内:一套产权界定方法和权利保护规范。
把现代性如此的定义加入到明清社会生活之中,这种做法需要加以限制性的说明。事实上,当时无人提出什么“权利倡导”,也无人依据目前人所熟知的权利—义务模式去考虑问题。因此,与其说明清社会内部孕育了现代性的需要,不如说当时社会日常的一些基本问题大概借用于现代性的策略来加以解决。换言之,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了一些结合点。这个问题也可以另一个事例加以说明。
在对所谓清代习惯法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习惯法的支配原则与官府之法的支配原则不尽相同。前者是一套实用性常识,其应用关乎民过生日用,因此主要受实用理性支配。后者则相反,作为一种精英常识传统,它的符号意味更强,文化选择色彩也更浓。通过对此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我还发现,尽管这两种常识传统从来不是互相隔绝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之间的联系终究是外在的。中国历史上既缺少一种关于习惯法的说明性学理,也缺少一个从事于这种探究和说明工作的群体,结果是,所谓习惯法只能是一种粗糙、好用的地方性常识,而无由成为一种精致、抽象和富有学理性的常识系统。(注: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第127-140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用一个反例来讲明这种情形,大家可以举出中国近代的习惯法整理运动。这场运动发生于中国近代法律变革之后,是新的民、商事立法的一个环节。在全国范围的调查过程中,习惯法初次被全方位地搜集和整理,并且依据现代民、商法体系加以分类。(注: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在北京政府司法部主持下进行的全国范围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其结果即是1930年出版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不只这样,在当时各地的司法审判过程中,习惯还被根据现代法理加以讲解,进而程度不同地融入于司法实践和新式立法当中。(注:作为中国固有规范之一的“典”被吸纳到《民法典》中就是一个好例。除此之外,《民法典》第一条即规定,民事没办法律规定者,适用习惯。)作为平时生活实践的民间习惯忽然获得这样关注,显然不是由于它们自己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是由于法律规范的整体构造改变了,由于这一变化,一向被官府视为细微末节而不加看重的“户婚田土钱债”事务开始具备特殊的重要程度,与这种事务有着直接关联的社会生活实践也被从新的角度重新加以理解。在此基础之上,作为民间小传统的习惯与新的国家法律渐渐被内在地联系在一块。
在明清社会内部发现现代性的成长点,这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它表明,传统与现代不必截然两分,“礼治秩序”中也会有“治法”的要点。反之,依据同一种逻辑,“法治”与未必不可以包容和吸收某种“礼治”的要点。
也是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区别了三种不一样的权力种类,即所谓横暴的权力、赞同的权力和教化性的权力。前两种权力另有专名,即专制与民主,后一种权力种类则为中国乡土社会所特有。在费氏看来,这种权力显然不是专制的,但更不是民主的,而是打造在他所谓“长老统治”的基础之上,是“无为政治”的一个结果,“礼治秩序”的一项内容。换句话说,教化性权力的社会基础,是乡土社会中的特定经济条件和社会组织结构。在那里,横暴的权力遭到种种约束,在人民的实质日常是松弛的和微弱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60-70页。)也是着眼于这一点,有人说中国虽没政治民主,却有社会民主;或说中国的政治结构分为两层,上面是不民主的,下面是民主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65页。)也有人觉得,与前现代社会中的欧洲人相比,中国人享有自由,一直都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注:譬如,孙中山先生即有如此的怎么看。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6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论与中国》,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年代的讼师与诉讼规范》,范愉译,载《明清年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持这种怎么看的人一般会注意到传统社会中的乡族、村庄、行会等一同体,强调其自治性质和它们对于来自国家的专制力量的消解用途。具备讽刺意味的是,“五四”运动将来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舆论恰好觉得,传统社会中的一同体如家族、行会等不只不是自由的保障,反而是自由的大敌,只有彻底打破这种所谓“宗法社会”的格局,个人才可获得真的的解放。中国现代国家就是在这套现代性话语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只不过,它最后并没达成任何有关个人解放的诺言,相反,伴随“宗法社会”的彻底瓦解,不只社会消失了,个人也不复存在。国家取代了所有,吞噬了所有。因此,毫不奇怪,在20世纪马上结束之际,当大家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并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认真检讨的时候,历史上的各种一同体,它们的自治性质,与它们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又一次引起他们的注意。(注:参见杨念群:《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办法及限度》,载《21世纪》1995年12月。)
在此,我无意对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加以论证,事实上,我并不觉得传统的中国人(即便是在明清年代)具备与西方人同样的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当费孝通先生指出教化权力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70页。)或者,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未尝自由亦未尝不自由的时候,我想,他们都意识到了中国社会情态的复杂性,意识到简单地用自由、民主一类价值去衡量中国传统社会的危险。尽管这样,大家仍可以去构想一种经由“社会”来达成的个人自由,而且,无论大家赋予这个“社会”哪种现代含义,在它与那些渊源久远的民间社会组织形式之间,是可能存在某种联系的。(注:梁漱溟:注譬如,孙中山先生即有如此的怎么看。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6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论与中国》,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年代的讼师与诉讼规范》,范愉译,载《明清年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第254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大家可以说,现代法治也可以在传统的礼治秩序当中汲取养分。
五
中国近代革命和中国现代国家,都是在一个历史进步论的宏大理论笼罩之下进步起来的。这种理论力图叫人们相信,人类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当中获得进步,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现代取代传统,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规律,是人类进步的势必结果。受这种宏大理论支配,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现代性话语,这类具体理论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假定传统与现代完全不同,相信前者势必为后者所取代。在本文前面所介绍的费孝通先生对于所谓“乡土中国”的描述里面,就隐含了如此的理论逻辑。在那里,正如大家所见,“乡土社会”及其“礼治秩序”是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定义区别中被把握和说明的。因此,这里的问题并非费氏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描述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或者,他从中国具体社会中提炼出来的定义具备多大的说明力,而在于,这种对中国社会的察看和解释说明在多大程度上遭到作者本人理论“前见”的影响和扭曲,与,一种贯穿于语词和定义结构中的理论可能在多大程度上遮蔽社会现实,又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大家的想象力。
通过把定义引入历史,使之情境化、相对化,本文试图说明,费氏笔下的“礼治秩序”其实是一个人为架构的虚幻实在,支撑这一架构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事实上并没有。相反,实质状况可能是,“礼治秩序”中有“法治秩序”的成长点,“法治秩序”也可以从“礼治秩序”中获得养分。在“礼治”与“法治”、传统与现代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些大家从来没注意到的结合点。假如真是如此,大家便不能不重新反省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不能不重新看待和评估今天仍然备受压制的各种民间常识形态,不能不重新反省和调整大家对待历史传统和民间社会的立场和态度。毕竟,大家今天的历史处境和存活状况,与大家对历史、社会、过去和将来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意识不到这一点,大家就将既失去过去,也失去将来。
从“礼治”到“法治”?
点击数:268 | 发布时间:2025-02-06 | 来源:www.fklsfc.com
- THE END
声明:本站部分内容均来自互联网,如不慎侵害的您的权益,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
-
- 学习交流 -
-
欢迎加入国家人事网,与万千考友一起备考

- 成考路上不再孤单
专业院校
-
关注“考试直通车”
-
领取备考大礼包
-

点我咨询
返回顶部
Copyright©2018-2024 国家人事网(https://www.zbxggc.com/)
All Rights Reserverd ICP备18037099号-1

-

国家人事网微博
-

国家人事网